1763年,大卫·休谟(1711-1776)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巴黎,官方身份是英国驻法大使秘书(后晋升为临时代办)。不过相比而言,他的另一重身份——英国当世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更令惯于“追星”的巴黎士女如醉如痴,其中“最真诚的崇拜者”是蓬帕杜夫人。据休谟事后向友人吹嘘:“当我被引荐给蓬帕杜侯爵夫人时,如众星捧月般环绕在她左右的那些溜须拍马之徒都对我断言,从未见她对任何一个男人说过这么多话。”
照英国传记作家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看法,蓬帕杜夫人不仅是国王路易十五的首席情妇,而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首席赞助人。她在宫廷接见休谟时“公开示好”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包括启蒙哲人在内法国朝野的共同心愿:通过文化交流弥合两国长期的政治(及军事)冲突。在他们眼中,这位身材肥胖、笑容可掬却又满腹经纶、妙语连珠的苏格兰“文人”(man of letters)最适合充当英法文化使者——事实上,也正是在此期间,他收获了“好人大卫”(Le Bon David)的令名。
为休谟奠定声望的是他新近出版的六卷本《英国史》(1754-1761)。正如欧内斯特·C.莫斯纳在《大卫·休谟传》(周保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所言,“休谟在巴黎的风行主要得益于当时正在盛行的‘英国狂’(Anglomania),得益于人们对抽象思辨和历史的兴趣。”早在动笔之初,休谟私下便对好友勒勃朗神甫(Abbé Le Blanc)宣称,他预见到《英国史》将在法国“大获成功”。勒勃朗是著名艺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名受蓬帕杜夫人赞助的巴黎“文人”。他最早将休谟的《政治论文集》(Political Discourse)译成法文,大受欢迎。勒勃朗有意承担翻译《英国史》的任务,后来由于个人原因被迫中途放弃,于是将这一任务转交友人小说家普雷沃神甫(Abbé Prévost)。
普雷沃其时年事已高,动作迟缓,六卷本首部《斯图亚特王朝》直到1760年方才面世,然而许多法国热心读者已急不可耐,乃转而搜求英文原版。经济学家、《百科全书》词条编纂者莫雷莱(André Morellet)——他被称为“最后一位启蒙哲人”——在回忆录中透露,1760年身陷巴士底狱时,他如何说服老友、法国书报总审查官马勒泽布(Malesherbes)为他“捎去”两部著作——塔西佗的《历史》和休谟的英文版《英国史》。法兰西学院院士、哲人沙特吕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则对友人声称,他自学英语只为“阅读休谟史书”。结识休谟后,沙特吕侯爵在一封书信中告诉这位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在文坛,就像耶和华在希伯来人中一样值得尊敬”。重农学派领袖、后出任路易十六财政总监的杜尔哥(Turgot)对休谟的著作也推崇备至,认为“无论从标志性事件还是从非凡人物来看,(斯图亚特王朝)都是英国现代历史中最有趣的”,其重要性非比寻常——只是普雷沃译本差强人意,倒不如他本人“亲自动手翻译”。
普雷沃病逝后,由贝洛夫人(Mme Belot)主持翻译的《都铎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相继出版,进一步巩固了休谟的声誉。哲人爱尔维修(Helvétius)于1763年初致信休谟,对他在历史书写中展示的“公正的哲学精神”极为钦佩。同年8月,沙龙男主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赞誉休谟为“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为休谟在史书“序言”中警告说,所有预想人类天性发生巨大改变的政府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虚构”,正中时代之弊病。1764年,著名作家、第戎高等法院德·布罗斯庭长(président de Brosses)——“拜物教”(fetishism)一词的发明者——在写给休谟的信中评价:“您十分真实地描绘了您的国家,不带偏见地呈现出贵国的社会礼仪、特质和政府的真实情况”,并断言其成就甚至“胜过塔西佗”。
“公正”和“不带偏见”是休谟历史著作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国哲人对他赞赏有加的主要原因。正如《百科全书报》(Journal Encyclopédique)刊载的一篇评论所言:“光荣革命”之后,在休谟之前,几乎没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写史”——其中绝大多数如伯内特(Gilbert Burnet)之流,一边接受新政府资助,一边肆意吹捧“新君”奥兰治亲王(即位后称威廉三世)。相反,休谟秉笔直书——他一向主张“历史学家的首要品德是真实和不偏不倚,其次(才)是有趣”——称颂查理一世“拥有一位好国王的美德”,认为这位合法君主遭受克伦威尔及其党羽的政治迫害:他在缺乏合法权威的情况下受到审判,并被无端处以死刑。休谟宣称,人们发现“这位君王立于断头台前更显伟大:他在统治期间经历了胜利的荣光与失败的不幸,而这些都不及他此刻的坚定、慷慨与正直”。英国国内不少人指责休谟为一名被斩首的国王“洒下同情之泪”,更指责他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饱含怜悯”,并据此赠予他绰号“老妇人休谟”。而前耶稣会士、法国著名文人切鲁蒂(Joseph-Antoine Cerutti)则慨然为之辩护:“休谟先生的史书可以被冠以人类理性书写的《英国激情史》(“History of English Passions”)……这种单纯的善良使他的公正更加高尚,也使他的哲学更加感人。”
与历史时序不同,《英国史》采用“倒叙”手法:始于斯图亚特王朝历史(两卷),次及都铎王朝史(两卷),最后是凯撒入侵英国史(两卷)。本书不仅考察时人的生活方式,也详细刻画当时的贸易和学术状况、宗教及政治纠纷——远超以往帝王功业史的范畴。此外,除了忠实再现历史,臧否人物也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比如:在控制欲极强的伊丽莎白女王治下,酷爱自由的英国人逐步“丧失了所有自由”;首创共和的“护国公”克伦威尔其实只是痴迷权力却“昧于大势”的伪君子。
休谟坚信,自由是培植心智生活的先决条件。正如他在《论艺术与科学的兴起与进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文中所言,“在任何民族中,如果这个民族从来不曾享受过一种自由政治的恩惠,它就不可能产生艺术和科学。”休谟这一观点不仅与启蒙时代精神相契合,而且也顺应了社会进步的潮流: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艺术与科学进展较为缓慢,它们需要一个长期稳定且宽松的政治环境才能臻于成熟,步入其黄金时代(如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十七世纪的荷兰共和国)。
除了自由之思想,休谟也倡导独立之精神。他秉持史家的良知和责任,下笔往往独出己见而不肯随俗,正如《百科全书报》评论文章所说,休谟是“第一位敢于宣称君主制与共和国一样有利于艺术、哲学和商业进步的英国作家”——事实上,和前辈孟德斯鸠以及稍后的爱德华·吉本一样,休谟坚信文人在君主制下受到的“礼遇”远胜过其他政体(如克伦威尔的“英格兰共和国”或大革命后的“法兰西共和国”)。他在探讨英国内战起因时曾以冷峻的笔调写道,“让人民不知道他们服从的界限,远比让他们知道君主应该遵守的界限更安全。”
根据传记作家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的看法,休谟的历史著作,就像他的随笔一样,是“沟通学术界和大众对话之间鸿沟的尝试”——在《论随笔写作》一文中,休谟曾经坦承:作为跨界的文化使者,“我认为推动学术领域和日常会话之间的良好交流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两者息息相关相互依存”。休谟选择这一体裁,显然受到法国哲人的影响。早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代,他对蒙田和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便产生了浓厚兴趣。最早吸引他的是迪博神甫(Abbé Dubos)《对诗歌和绘画的批评性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日后休谟曾引用书中名言:“灵魂的欲求不下于肉体的欲求,人类最大的欲求之一便是让其心灵始终处于忙碌状态。”
此外,休谟熟读培尔(Pierre Bayle)的《历史和批判辞典》,尤其赞赏培尔对宗教的批判态度,曾由衷赞叹“培尔那里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宝藏!”照彼得·盖伊在《启蒙运动》一书中的看法,休谟不无惊喜地“发现培尔能够与自己相伴一生”。受培尔启发,休谟对蒙田著作产生浓厚兴趣——1737年,当休谟首次隐居法国乡间写作《人性论》时,蒙田名篇《为雷蒙德·赛朋德辩护》是他案头常备之书。1742年,休谟发表一篇有关蒙田的随笔,以此向蒙田致意。毫无疑问,蒙田启发了他的怀疑主义精神:所谓“休谟之叉”(Hume’s fork)——将人类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学和逻辑命题知识,另一类是经验命题知识,并且承认后者具有“不确定性”,很大程度是蒙田“吾何知”(Que sais-je?)的2.0升级版。
相比于蒙田,休谟对笛卡尔“用力更勤”——为了研读和批判其唯理论(Rationalism)。他的隐居地选择在拉弗莱舍(La Flèche),据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交代,原因是此地有一所耶稣会士学院(笛卡尔曾在此学习)——学院馆藏图书四万卷,使得休谟的哲学和历史著述如鱼得水。笛卡尔以论辩形式写就的《沉思录》,对休谟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影响尤为显著:即以(自然)科学的精确研究法施于历史及哲学等人文学科研究。在包括休谟在内的十八世纪哲人看来,历史著作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历史是智慧的伟大情人”(great mistress of wisdom)——在人文科学诸门类中,它可能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门:“历史是为了未来而加以诠释的过去”(history is the past interpreted for the future),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事件”。
休谟为人平和,但他的宗教观相当激进,被对手贬称“异端”(The Infidel)。他认为就其本质而言,宗教乃是“一种迷信”——源于原始人对外界环境(自然)的无知而产生的恐惧。作为迷信的宗教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政治上都“极其有害”,特别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教,它比西方古代的多神教(异教)更具压迫性,更容易造成人民的分裂。同时,由于宗教信仰并非理性的产物,因此,无法基于事实来支持或反对它——从这一点来看,用严密的论证劝说别人信教或不信教都是极其可笑的行为。据此,休谟大力倡导宗教宽容。他的名言是,“一般来说,哲学错误只是荒谬可笑,而宗教错误则极其危险。”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以反宗教为己任的法国哲人与休谟共鸣最多。伏尔泰是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先他曾与休谟有过交锋——伏尔泰在史学著作中对休谟“恩主”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进行人身攻击,休谟也曾愤然发起反击。尽管如此,在拜读《英国史》后,伏尔泰却不计前嫌,主动向休谟示好:“人们无法再为《英国史》增誉,因为这部作品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上佳之作……人们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哲学家才应该写史书,因为他们不受任何一个国家与任何一个政治或宗教派别制约。”在年迈的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沙龙中,伏尔泰曾将休谟《英国史》与爱尔维修的《论精神》(De l'esprit)进行对比,认为“休谟先生展现出英国人的智慧和胆识”,而爱尔维修“没有表现出这些品质的二十分之一。但他在法国却受到迫害,他的书也被焚毁”——这一切都证明“英国人是心智成熟的大人,而法国人不过是幼稚的孩童”。
在启蒙哲人中,孟德斯鸠最早发现并认可休谟的天才。1748年,孟德斯鸠读到休谟近著《道德和政治随笔》,对“论国民性”一文印象尤为深刻。次年,在致休谟信中,孟德斯鸠不吝溢美之词:“在这篇优秀的论文中,您赋予道德因(moral causes)而非物理因(physical causes)以更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如果我有资格评判的话,您直指事物的要害,这是很不容易的:您的写作方式展现了大师的手笔。”与之相应,休谟对孟德斯鸠也怀有崇敬之情。同样在1748年,被法国当局封禁的《论法的精神》在日内瓦面世,正在意大利进行外交访问的休谟第一时间入手此书。他不仅“怀着极大的兴味和关切”读完此书,附带还完成一份意见反馈表。1749年末,休谟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促成《论法的精神》(两个章节)在爱丁堡翻译出版。后来,他又以书信形式将批评意见反馈给孟德斯鸠——后者惊喜地发现:休谟的评论“充满了真知灼见”。于是,孟德斯鸠欣然接受休谟的通信邀约,直至这位长者于1755年辞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照勒勃朗的看法:“在欧洲,您(休谟)是唯一一个可以取代孟德斯鸠男爵之人。”
当然,除了精神气质的契合和思想观念的共鸣,休谟与法国启蒙哲人也存在大异其趣之处。比如他的宗教观是“温和的不可知论”,而启蒙哲人多奉持无神论(日后马勒泽布的曾孙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论断,正是激进的反宗教思想促使了大革命兴起)。休谟能够跟法国耶稣会士友好往来,但启蒙哲人与之不共戴天。此外,更主要的不同在于,生活在“理性时代”的启蒙哲人普遍相信,“人类的高贵之处在于理性”,而休谟则认为,人类不过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受激情驱使和主宰的动物——“人的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只是在激情过后,为了替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人才会运用到理性。
正是基于对理性的盲目崇拜,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哲人往往乐观地相信人类社会及道德会不断进步并臻于完善,对此休谟并不认同。根据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惠兰(Frederick G. Whelan)在《休谟及其同时代人的政治思想》一书中的观点,受杜尔哥影响,怀疑论者休谟并不相信任何“无限趋近完美”(“perpetual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的“进步理念”(“idea of progress”)。在休谟看来,人类的行为往往受“信念”驱使,因此若想推动社会进步,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信念”——照他的看法,“大多数信念之所以合理,仅仅是因为它们管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以常理和人情(moeurs)对抗唯理论的休谟不仅是情感主义者,而且也是实用主义者——他号召人们“做哲学家,但做学问的同时,还要堂堂正正做人”。
作为十八世纪的情感主义者,休谟对女性的友善和尊重是他在巴黎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我的读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他在一篇随笔中宣称,“严肃地说,我支持这样的观点:女性尤其是有思想的、受过教育的女性(我自己也是只对这些读者写作)是所有风雅文学的主要对象——与同等理解程度的男性相比,女性是更好的评判者。”事实的确如此。在所有法国读者中,休谟认为最好的评判者是布夫莱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1761年,阅读《英国史》后,伯爵夫人致信休谟,“我无法用言语向您传达我的感受。我太感动了,深深地被感动。这种感动在我心中久久回荡,以至于某种意义上变为一种痛苦。我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内心充满爱和善意……先生,您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您所描绘的画面优雅、真实、又充满活力……毫不夸张,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圣人的作品。”
布夫莱尔伯爵夫人是巴黎名媛、沙龙女主,卢梭、狄德罗以及博马舍(Beaumarchais)等“百科全书派”皆是她的座上嘉宾。她和休谟迅速建立起一种“友谊关系”(且维系终身)——传记作家莫斯纳(Ernest Campbell Mossner)曾意味深长地说,“这种关系要比友谊更加亲密”——休谟临终之前分别向亚当·斯密、达朗贝尔(d’Alembert)等挚友致信,其中便有一封书信致伯爵夫人,坦言“我看到死神正在悄悄地逼近,但我既不感到焦虑,也没有什么遗憾”,可见这份情感分量之重。1765年,在外交官休谟离任返回英伦之际,正是这位夫人将她的“受保护人”卢梭托付给“好人大卫”。休谟不顾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友人劝阻(他们对他讲述“农夫与蛇”的寓言),决定携带其时受法国政府通缉的卢梭“私奔”——由此引发日后闹得沸沸扬扬的“卢梭-休谟之争”。二人大打笔战,大半个欧洲的文人哲士各执一端(连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也牵涉其中),由此“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面临土崩瓦解,欧洲启蒙运动亦遭受重创。
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休谟的好友富兰克林作为美国驻法公使出使巴黎。据目击者声称,这位美洲启蒙哲人(被誉为“美国先生”)在法国朝野大受欢迎的盛况,唯有当年的休谟“差可比拟”。
同年,休谟在爱丁堡家中安然去世。据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医生所言,休谟在离开人世之际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认为自己一直致力于使自己的同胞变得更聪明,特别是把他们从基督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只是他尚未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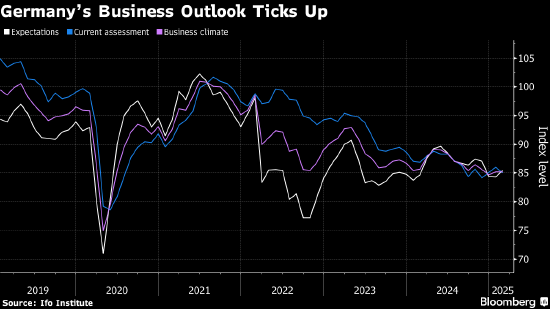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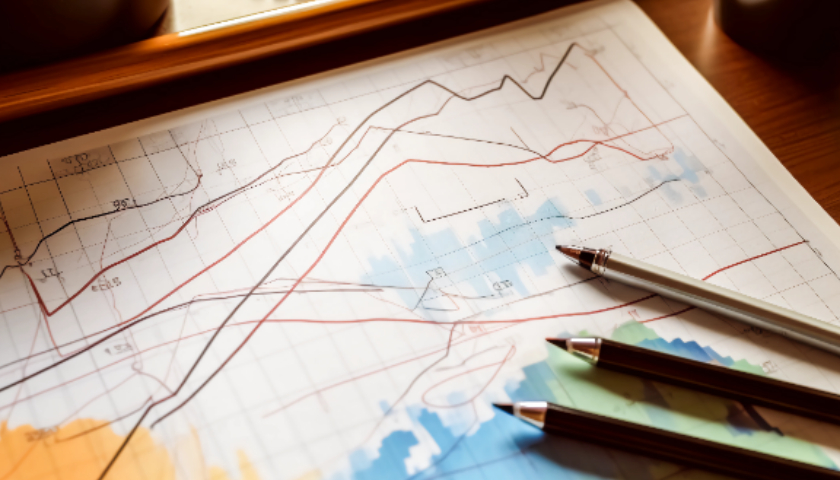
 冀ICP备15028771号-1
冀ICP备15028771号-1